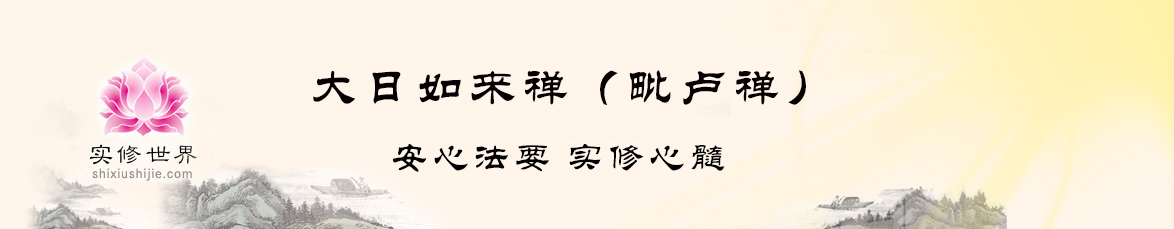
最新发表
修行报告
一.主要修行经历
1991大学毕业,看到南怀瑾老师的一套五本书,很感兴趣,主要看了《金刚经说什么》和《如何修证佛法》,但并未真正开始修行。
1996年至1999在澳洲留学期间,加入了基督教,因天性重诺,回国后虽无法参加教会活动,仍严格遵循教会的一些原则,如日常生活中的不抽烟、不饮酒、不喝咖啡、不喝茶等。但回国后的工作生活中,感觉这些逐渐成为困扰,仿佛自己是玻璃屋中人,再加上因工作上的压力求助教会而不得,身心状态进入低谷。
当时有一个大学同学从美国回来与我同住,偶尔会聊到她在美国的同学ZX及其先生YHY的一些情况,以及她自己信的密宗和青海无上师等等。某日闲聊中,她再次讲起这二人,我突然问道:可否带我去见见YHY?并无打算,也无计划,当时脱口而出,自己也觉奇怪。
第一次见面在老师那里倍感委屈,哭了一场,老师当时应教授了打坐之法,但回来后并未实践。半年后,自己又独自约见了老师一次,并决定开始打坐,自此未再间断。
当时也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我要修行”或我要怎样的发心,不过如老师所言,我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一路探索,拿到后若觉不是即刻就扔,继续探求。记得在澳洲教会学习时,老师讲课说:我们信神、听神的话,死后就会回到天父的身边,得到奖赏。我问:为何那些并不知道有神、也不求死后回到神身边但自发行善的人不能得奖赏呢?在我看来,我们这些信神的人目的性太强了,所做的一切好事不过是为了得到神的庇佑和奖励,若我是神,我必认为那些不信神而行善的人要比我们这些信神的好,而且应该得到更高的奖励。
我的许多问题教会无法回答,与老师见面后,玻璃屋被打破,知道向内求方可获得一切答案。十几年来打坐修行从未间断,在功夫上有了一定的累积,但由于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只要坚持日日打坐,只要功夫到了自然会有成佛的一天,因此在理上的探求十分欠缺。
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隔阵子与老师见面一次,在北京生活工作时频率高些;中间有几年去了外地工作,则回京时与老师见面,除了打坐修行,与老师聊的更多的是工作和生活。因对理不甚重视,所以从来也没对自己所在的状态做什么区分,不像现在很多师兄,见面就问是在六还是七八或是已见了自性?只觉得那是多么高的状态,自己老老实实打坐就是,到了那一天自然会知道。但对于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是清晰的,所以从未怀疑过老师(虽然那时还对老师直呼其名),也从未想过要去找寻其他什么方法。
2013年从上海回京见老师,聊到工作上不甚开心,在考虑辞职,老师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去同有三和工作。此前听老师说起过LLH老师和同有三和中医,也只是听听而已,不觉得与己有什么关系,老师这么一问也是让我一愣,低头想了一会儿,回说:看了看自己的心,不抗拒,但也没什么兴趣。老师让我不忙决定,抽空以病人的身份去南宁体验一下。2013年底去南宁,做了五行针灸治疗和手法治疗,治疗本身并未让我感觉太深,但两位年轻医生表现出来的彷徨、苦闷却让我惊讶:生活在开放开明、可以自由选择的21世纪,为什么还有年轻人活在如此的自我桎梏中?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我要带他们看世界的另一面,过心灵开放自由的生活!
从南宁回来,去了北京,见了老师的第一句话是:我愿意去同有三和……2014年6月,正式开始在同有三和安徽汤池馆上班。一路磨来,这是修行进步最大的三年。
这三年,懂得了在完全知道对方的缺点而对方未见得完全认可你的情况下还能为对方着想才是真正的包容;懂得了包容别人其实正是超越自我;懂得了当你口口声声说无我的时候正是有一个大大的我,而当你真的无我的时候却能嬉笑怒骂、随意挥洒、任人评说……
也是在这三年里,与跟随老师学习的其他师兄们得以相识交流,放弃了所谓“平等”的概念认了老师(以前对老师都是直呼其名的),才与老师的管道真正接上;并且从师兄们的修行中,认识到自己在理上的欠缺,从师兄们的精进中看到了自己的不精进,心生惭愧……
现下很明确:生活是修行,工作是修行,一切都是修行。认真做事,但不执着于结果。
日常修行功课:每天早晨打坐两小时,其中坐约一个半小时,收功约半个小时。
晚上有时间,会看《如何安心如何空》,或是南怀瑾老师、谈锡永老师的书。
除同修外,不喜欢主动与人谈修行的事,也不会劝人修行,除非别人主动问上门来。
二、目前的证量
1、
形而下的证量
持咒时,膻中处心能很快升起,全身能量调动,近期的状态是从膻中处升起的能量向上直到眉心,在眉心处阻力大,艰难地继续往上;头顶百会处有能量外散。
躺着吐气时,则背后脊柱的感觉更为强烈,能量沿脊柱由命门之下往上升,右腰眼劳损处有时会刺痛,至脑后玉枕穴(大概后脑下部中间部位)受阻,整个后背发热明显;肩颈有僵硬,但吐气打坐一段时间,肩颈能量排出后会轻松,但过一阵后又会僵硬起来。尾椎骨时会有隐隐的痛。
有时吐气睡着了,睡中朦胧感觉有细细的能量顺后脑勺往头顶走。
吐气时,数次闭着眼感觉到眼前变光明,持续一会儿回复正常,但都是在白天的体验,未尝有在黑暗中现光明的体验。有一次参加其他师兄与老师的见面会,闭眼听师讲话,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坐下的工作生活中,已基本能做到在状态,大脑不起分别意识,事来即反应,事去即放下,有所思考时也是由心而起。对于他人表现出来的言行有比较强的觉察力,可以看到言行背后的原因,表现为看问题一针见血、一插到底,但不具备像BY师兄、QF师兄那样看到别人心起处的能力,如心动、心疼等等。
2、
形而上的证量
反复看《如何安心如何空》对各学部的介绍,但自己的修行过程并不像具备书中那般清晰的步骤。可以确认第六识已破,因很清楚地会用心。是否超越第七识,回想起跟老师的一次汇报:坐中不断进行“观”和“返观”的操作中,有一个“我”在观,然后从这个“我”里要再分一个小我去返观,但一天突然意识到分不出去了也不需要分出去了,就是一个完整的我可以觉察到以前“观”和“返观”加起来的全部……老师笑而不语,也许这便是超越了第七识?
但那之后相当长的时间是不稳定的,时会被升起的情绪能量淹没。老师2016年10月在龙山禅修会上棒喝:恐怕还是第六的分别识吧!龙山禅修会后,多了对自我的反观和反省,每日在状态的时间逐渐增长——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下“在状态”:该做什么做什么,由心而起的能量将整个人包括大脑罩在里头,脑袋因此反而觉得有些闷闷的、笨笨的;事来时由心而起自动反应。
今年起感觉到心口部分又开了一层,一段时间左胸骨处有比较强的痛感,而且也会敏感到别人的痛(以前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通过老师的指点,慢慢开始体会),心开后觉得整个人又较前光明许多、定许多,有情绪也就是心口处能量起时都能清楚觉察,前台的能量和后台观察的主体是分离的;但继续探查能量的源头时,感觉心口处是个深洞,能量似乎是无中生有的,不是顺着心口往下挖就能找到,但从心口移开去看别的地方时,也看不到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试图去找“主体”或“我”时,“我”不在脑子里,不在心口,四处看看,似乎有一个模糊的大大的我在身后罩着,但又触及不到。老师说:你现在拿着那个我,一放就破掉了……可确实不知道怎么放。
近几个月来在排头上的东西,打坐时会出现昏沉,所需睡眠时间增多。今日早上开始,两个太阳穴和头后部开始出现一阵阵的刺痛(确定不是感冒或生病)。
三.是否参加过精读小组等的活动
没有参加过精读小组的活动。一直认为修行是个人的事情,自己坚持、自己努力,有了问题就直接向老师请教。当初刚开始组织精读小组的学习活动时,有师兄邀请参加但拒绝了,感觉这样的活动会有帮助但也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这次申请参加小组学习,一是看到确实有不少师兄在小组学习中受益、进步很快,另一个是老师提议。而不愿主动与他人就修行做交流恐怕也是自身存有障碍,所以愿意面对并接受挑战。
四.目前想要解决的问题
2017年6月22日

全部评论
实修世界要发表评论,您必须先登录。